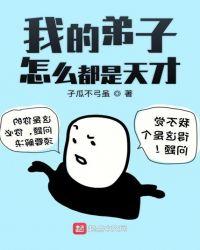墨澜小说>梁臣美景夜公子 > 第239章 醒来近黄昏(第1页)
第239章 醒来近黄昏(第1页)
定州镇城,业城东城主街转角处坐落一家气派的三层木楼,楼体雕梁画栋,彩锦飘舞,客人只见进不见出,门口的伙计趾高气昂,似乎今日生意不错。
木楼对面则是一间很不起眼的小门面,门脸装饰已经相当的陈旧,店内的伙计趴在柜台上打着哈欠,店掌柜正有一下没一下地悠闲地翻着书册,与对面的繁华相较,这里仿佛被人遗忘了。
不过,千万不要被这惨淡的生意,冷清的表面所蒙骗,这里可是城内数一数二挣银子的旺铺。只是现下的时段,并不是这间铺子最佳的营业时间。
一早一晚,铺子的客人们除了打扮独特外,或蒙脸,或带兜帽,个个遮遮掩掩,鬼鬼祟祟,生怕被人认出似的出入于店铺的侧门及后门,也是络绎不绝,出手阔绰。这家铺子的生意不比对面那家业城最大的青楼差。
这就是城里老字号药铺,名曰颐草斋,传承三代历经近百年。它与对面同为百年的青楼迎春阁,相辅相成,不离不弃,乃业城最负盛名的两个传奇企业。
往常这个时辰,颐草斋不管前后堂都会比较闲,基本没有病人来此处看病抓药。然而今日,颐草斋后堂显得格外热闹,布行的刘员外进去了,没过多久他就带着兜帽神情萎靡地从后门偷偷摸摸地溜走了。车行扛包的力夫,王大胆随后闪了进去,良久,披着块破褡裢面色蜡黄,踉跄着摸了出来,紧接着木器行的吴师傅按着个大斗笠又进去了。。。。。。。。总之这一下午,颐草斋后堂陆陆续续地就没个清闲,三教九流,贩夫走卒个个行当的都有,每个人且是偷偷摸摸进去,歪歪斜斜出来,甚是诡异。
“呸~~这群不知羞耻的臭男人,也不知道在里面鼓捣些什么?”
临街的大婶坐在自家门前纳着鞋底,在这里观察颐草斋后堂小门整整两个时辰了,眼见那么多猥琐的男人进进出出,恨恨地啐了一口,缝针被狠按入鞋底,几股粗线抽的那是沙沙得响。
“还能鼓捣个啥!肯定是前面那些骚狐狸勾搭的呗,这不知羞耻的郑半仙专给那些骚狐狸看病,这怕不是哪个骚狐狸染个啥见不得人的病,传给这些臭男人,郑半仙挨个叫来给瞧病呗。”
旁边坐着看热闹的另一个大婶一脸鄙夷地说道。
“嘿嘿~~有意思哈,那个扛大包的王大胆居然和刘大员外成了连襟,这些男人还真是不挑啊。”
“就是,那个吴老头老得都快入了土,还那么风流。见着了银子,这些骚狐狸什么客人都敢接,也不怕吴老头当场归西惹上了官司。”
“呸~~~”
二人又齐齐向着颐草斋后堂方向啐了一口。
“哎?我说呐,午时里听说有不少官兵抬着两个人从前边进了医馆,这会儿都没见着人影,不会是假的吧。你家离得近,知道咋回事吗?”
“确实是有一男一女被抬了进去,浑身的血啊,那男的上下衣裳撕得跟布条一样,那女的身上缠着纱布,二人皆是不省人事。瞧瞧,这也有几个时辰了。”
二人齐齐伸长了脖颈,扫视了眼医馆几侧开口处的动静。
“啧啧啧~~现在的年轻人真会玩,这下玩大了吧。”
“谁说不是呢!”
天色都有些擦黑了,这两位夫人似乎忘记了开饭的时间,仍饶有兴趣地坐在门口叽叽咕咕说着小话。
此刻的颐草斋后堂里,业城夜影司千户郑白芷正坐在桌子一头用惊愕的目光看向桌子的另一头,只见桌上饭碗摞得老高,一个披头散发的人正推开眼前的十余碟空盘子,纤长的手指捏来一只杯盏,低头撮口茶水,又如饿死鬼投胎一般疯狂地扒着碗里的饭。
“添饭,添饭~~再加点菜。郑大人,别那么小气,再给要个大些的席面,我还没吃饱呢。”
趁一桌饭菜一扫而空的当口,千面姬将那人乱发梳顺了挽成简单束发,一张惊世骇俗的俊脸显现,即便腮帮子此刻鼓得老高也难掩他的英俊不凡。
就在不久前,一直昏睡的秦牧玄终于苏醒过来,而睁开眼见到千面姬的那一刻,他嘴里却只吐出了俩字。
“好饿~~”
字正腔圆,表达明确。
郑大人立即叫伙计到对门迎春阁给他定了一份丰盛的饭食,然而当郑大人兴冲冲地询问秦牧玄“病情”时,却发现那一大碗饭和几个小菜已然被一扫而空了,眼前这个病人正用筷子敲着碗大喊着加菜加饭。
郑大人无奈,只得又叫伙计到对门去定了一份大些的席面,因着这事儿,伙计还被对面老鸨狠狠奚落了一番,说是把他们迎春阁都当成什么了,酒楼吗!!
然而面对大快朵颐,嘴巴塞得满满的秦牧玄,郑大人楞是没说上几句话,这不!又得给这个家伙去再定一个席面。
这哪是人,分明是头牛嘛,有几个胃能塞下这许多饭食。郑大人对自家多年的行医经验产生了深深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