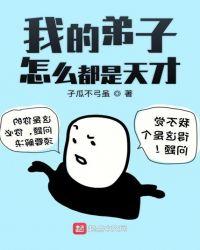墨澜小说>当万人厌嫁给朝廷公敌后 > 第 45 章 章四十五(第2页)
第 45 章 章四十五(第2页)
谢岁全将那哼哼唧唧当做耳旁风,老神在在坐在马车内发呆,还伸手将那颗正在磕头的脑袋提了一下,免得对方继续拿脑袋撞车厢。
若是撞了一头包,到时候傅郁离找他麻烦,那可得不偿失。
大抵是言聿白的动静太大,马车口的帘子骤然让人一掀,驱车的人恶声恶气道:“叽叽歪歪干嘛呢?再作妖把你杀了丢路边给野狼吃了!”
手边的少年身子一缩,开始发抖,谢岁拍了拍他的脑门,随口道:“义士就别吓唬小孩了,你已经带着我们已经走了六个时辰,如今已离金陵城百余里,何时才能见到王爷?”
“别废话,再多话把你也杀了。”那人粗声粗气放下帘子,在外头像是骂了声什么,随后马车跑的更快了。车厢内无比颠簸,谢岁感觉自己都差点被晃吐了,在马车狂奔的声音里,隐约有追击声跟在后头,倒像是禁军赶过来了。
言聿白也察觉到了,他又呜呜了两声,开始往马车前拱去,像是要借机从马车上滚下去。谢岁听着马车外杀手抽刀的铁器声,一把抓住言聿白的胳膊,将人按在车厢内,一拳打晕。
“谢公子,你这动手还挺快啊。”杀手的声音从车厢外响起。
谢岁一脸漠然,“他太吵了。后面可是有追兵来了?”
杀手不答,谢岁继续道:“听声音不下二十骑,下车,不然我们跑不过他们。这里距离你主子的驻点还有多远?”
那人依旧不答。
谢岁起身,抬手扯掉蒙眼布帛,下一刻,一股冷气袭来,随后一把长刀带着轻吟声抵在他眉心,“你想记路?”
谢岁眼也不眨,“我大可以将眼睛蒙上,只要你能带我们两个瞎子逃出去……只是如今你带着我们两个累赘,真的能从禁军手里逃出去吗?”
男人盯着谢岁,马车依旧在疾行,谢岁将布帛缠在手上,面不改色的将一侧晕倒的言聿白拉起来。
“我都已经杀了裴珩,便没有退路可言。”谢岁冲着男人轻笑一声,“你放心,我比你更想活,更想出人头地。”
马车嘶鸣一声,片刻后,马儿发疯似的冲着山路疾驰而去,留下几条沉重的辙痕。二十余骑追查而来的禁军,追着马车疾驰而去。
而官道侧的小路内,男人扛着言聿白,带着谢岁深一脚浅一脚的开始赶路。
没两步,言聿白醒了,男人便将小书生丢地上,提着刀赶羊似的驱他走。谢岁拄着竹竿,在旁侧看着言聿白对他怒目以对,小书生瞪着一双大眼睛,里头满满的都是愤怒,痛惜,以及不解。
谢岁全当做没看到,还冲着他懒洋洋的笑。有一搭没一搭的同杀手聊天,谈天下局势,说裴珩坏话,提自己命有多苦,就这样颤颤巍巍走了五里路,嘴还没干,腿实在支撑不住,光荣倒地,再起不能。
那杀手刚放下一个没多久,还没轻松多久,现在只能再背起来一个,一边背着谢岁,一边拿刀指着言聿白威胁他,翻山越岭,硬生生翻过了一个山头,走了一百多里的地,去掉半条命,方才在暮色四合时走到了终点——祥平镇。
确实宁静祥和,几百里荒无人烟,连个茶馆都没有。镇上的居民早早的都歇下,不见几盏亮灯。
言聿白也走到虚脱,也不用杀手拿刀指着了,几乎是手脚并用,在地上爬。
一把将谢岁丢地上,杀手再次揪住想要逃跑的少年,最后拖着两人停在一处隐蔽的宅院外,三个人歪在一处大喘气,什么杀人越货,谋逆造反都忘记了,六个手伸在门板上有气无力的拍门。
“来人啊!来人!”男人气都喘不匀了,晃荡着大门嘶哑道:“人带回来了!开门!”
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三个灰扑扑的人影难民似的伸出手指,争先恐后蹦进去,无头苍蝇似的在庭院里乱跑。
看守据点的侍卫吓了一跳,看这破破烂烂的样子,本想驱逐,在看清楚为首杀手的脸后,打了一个激灵,“头儿?你怎么这样了?”
杀手声音沙哑,一肚子火气,坐在大门口没好气道:“水!快上水!”
妈的,他怀疑谢岁是故意的。他扛着这俩废物点心爬了几百里,真的是累成一条死狗,别说发火,连话都懒得再说一句。
因而在手下问起该如何安排谢岁与言聿白时,杀手挥了挥手,表示随意。
喝完一大碗水后,便一头栽倒,不省人事。
谢岁坐在地上,他是三人之中体力消耗最少的,因着一路装死,也没怎么走路,故而看着还算比较精神。
他看着没几个人服侍的偌大庭院,估摸着这不过是一个接头地点。随后撑着竹竿,缓缓起身,摆出一副官威深重的模样,冲着府中的管家开口道:“我是你们王爷请来的贵客,这是我的书童。”
谢岁指了指趴地上,累的半死不活的言聿白,下巴微抬,“我等今日暂时修整,明日我要面见王爷,有重要消息通传!”
“还不快去备水备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