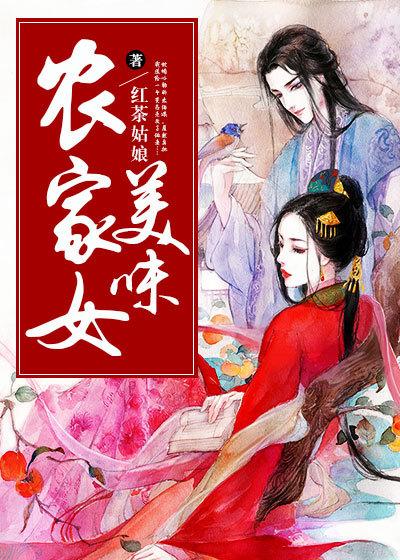墨澜小说>景云阕 > 第110章(第1页)
第110章(第1页)
露晞还俗后,怀着身孕搬到了张敬文在归义坊的宅子,两人也算续上了掖庭之外的母女之情。
只是因神秀大师抵京一事,我忙得不可开交,已经鲜少去到相王府中,实在难以抽身去看望她们。
正在瑶光殿誊抄佛事的经目,却被陛下唤至身前。她一面对我微微点头,一面对婉儿说道:“传太子妃即刻过来。”
“你替你五兄递来的上书,我已看过了。”
几日过去,陛下突然提及此事,我都险些要忘记了,忙回说:“阿兄心志不在朝堂,想要出家已经多年了。”
“你们韦家只此一个男丁,怎好叫他还未成家就踏入空门?”
“陛下巾帼之志,开天地未有之先河,又岂会把男人才能延续子嗣这般无稽之事放在心上?阿姊的孩子,难道算不上韦家的人吗?”我笑着反问道。
一句话道出了陛下心中深种的愁苦,她对着我坦然一笑,点点头道:“不愧是服侍在我身边的人。”
“陛下可会同意阿兄所请?”
“他也算有这个命数”,陛下微笑着说,“神秀大师抵京,会度僧千人。韦令裕又反复铺陈对大师之仰慕,我也愿意做个顺水人情,将你阿兄引荐给神秀大师。”
“团儿替阿兄多谢陛下。”我忙躬身行礼,心中喜悦非常。
陛下微微蹙眉道:“只是我不大明白,他既然与贤首国师的高足慧苑法师要好,却为何偏偏想依于神秀大师座下?”
“陛下有所不知,阿兄对佛典论辩的喜爱已是少年之事了,自他去了岭南,便对禅门修行情有独钟。自天授年间,陛下准许通信以来,他就时常问慧苑法师要些止观书籍。”
“原来如此”,陛下点点头,神情释然,“若说禅修之事,举国上下,无人能越过神秀大师去,看来韦五郎的佛门志向可不小。”
“阿兄之幸,在有缘等到神秀大师抵京,更在当今天子广布恩泽、亲善佛法。”
陛下不禁哈哈而笑,冲我嗔道:“这么些年了,还是如此爱哄我。”
正说笑间,阿姊随着婉儿急急步入殿中,婉儿重新侍立于陛下身侧,阿姊眉头紧锁,满脸焦急。
“起来吧”,陛下对匆忙跪下的阿姊道,“你们韦家有一件天大的好事,早些告诉你,也好叫你欢喜些。”
阿姊的神情瞬间松弛下来,展颜而笑,“多谢母亲。不知是何事?”
“神秀大师度僧千人,这是佛门中挤破了脑袋也难企及的幸事。我今日做主,韦五郎不必试经,可直接依神秀大师座下出家。”
阿姊的脸色由欣喜变得僵硬,她踌躇片刻,低声说道:“令裕是妾唯一的兄弟了,妾不愿韦家无后,不知陛下可否体谅?”
“这样的说辞,当真无趣”,陛下哼笑一声,“同为韦家的女儿,团儿就比你聪慧得多。”
阿姊一脸惊诧,她抬头看向我,责怨不由分说地写在脸上。
“陛下”,我不明白陛下为何要故意挑拨我和阿姊,出言缓和道,“团儿服侍陛下左右,才能有这般见地。阿姊一路陪着太子殿下走来,自然是顾及不到这些的,还望陛下不要苛责。”
陛下没有理会我,只是看着阿姊又道:“你不愿韦令裕出家为僧,甚至暗中联络祠部的官员,当真是为了你们韦家的香火,还是想让自己的兄弟早些步入朝廷,好助你这未来的皇后一臂之力啊?”
我明白了陛下的意图,她要借此敲山震虎,防止阿姊笼络官员、提拔外戚,形成自己的势力。
“陛下错怪妾了”,阿姊急忙又跪下道,“妾实在不愿韦家唯一的男丁就此出家。若说做官,做姊姊的自然希望弟弟为官作宰、光耀门楣,这并非什么大错。可陛下所说,妾欲与自家兄弟结党、外戚干政,实在冤枉。”
“陛下,阿姊所说是实情”,我顾不得其他,跪下求情道,“阿姊与团儿每每提及阿兄,也总叹息他还未成婚。况且阿姊若真有干预朝政的野心,为何偏偏盯着无意仕途的阿兄,不去寻些韦家的叔伯兄弟呢?”
婉儿也跪下求情,“陛下,太子妃……”
“不必多言了”,陛下打断道,“你们这一个一个的,倒像是太子妃受了天大的冤屈。作为东宫的女主人,还受不得这份猜忌,日后就更难统御后宫了。”
听懂了陛下的言外之意,我和婉儿急忙叩头谢恩,阿姊愣了一瞬,也跟着我们俯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