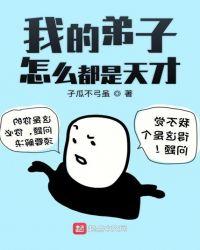墨澜小说>奸臣号废了,我重开[重生] > 第 124 章 问鬼一(第1页)
第 124 章 问鬼一(第1页)
经南亭新任仵作和乐无涯的一齐检验,仲俊雄的死因很快分明了。服食水银,乃至于此。以火煅丹砂,便能成此毒物。丹砂不算易得之物,但侯鹏经营药铺,对他来说,此物不难得到。但侯鹏和师良元从来与仲俊雄交好的,明面上并无杀人动机。就算当初他们有意找到仲国泰,套取了仲家人何时出发、何地登船的情报,也完全可以解释为“叔伯关心子侄”。而且,仲俊雄当初喝酒时并无甚异样。不少人亲眼见他好端端地上了船去。水银之毒,是在船行之后才发作。时隔一月,该销毁的证据早已湮灭。单凭一具尸首,根本无法定下侯鹏和师良元的罪。侯、师二人大可宣称,是船夫见财起意,谋财害命,才对仲俊雄下毒。若乐无涯传船夫到堂,船夫必然抵死不认。场面只会变成狗扯羊皮,互泼脏水。常年在水上跑的人,都有一副野调无腔的硬脾气,到时不仅要叫冤叫屈,恐怕还要痛骂他这县太爷一顿。既然早知道要挨骂,乐无涯就不特意去找这一顿骂了。至于仲家曾经的管家,乐无涯已经遣人去寻他了。但他的作用聊胜于无。他肯不肯实话实说都是问题。要是连着仲俊雄“联合外族谋杀朝廷官员”的罪名一起招供出来,他自己也要吃挂落的。……“现下便是这么个景况。”乐无涯晒着雪后明煌煌的大太阳,坐在廊下,吃着闻人约的汤面,无甚形象地盘着腿,将案情条分缕析地讲给仲国泰听。闻人约用软布擦着手,看着台上阶下的二人,是十足的无可奈何。大约两月以前,乐无涯和闻人约就“人贵自重”一事大吵了一架。争执过后,乐无涯反躬自省,知道自己那话伤了他的心,正筹划着要不要亲自去南亭书院,整个大排场,给足他的面子,将他哄回来,闻人约便拎着个点心匣子,一如往常地登了县衙大门。他站在乐无涯书房门口,腰背挺直,声声清晰道:“我想过了。我一开始对顾兄,确实是存了利用之心。但天地可鉴,我从未将顾兄视为棋子。顾兄是我……”他低下头,心中颠颠倒倒地转了几个来回。没等他想出能概括二人复杂关系的词汇,乐无涯便瘸着腿一蹦一跳地迎了上来,径直扑到了他身上去:“哈!自己送上门来了!”乐无涯这一扑,把闻人约的一切心思都扑散了,只余下满腔简单的欢喜。二人就此言归于好。可就在方才,仲国泰没来之前,二人又争执了一场。起因很简单:闻人约不许他将仲国泰留在身边。闻人约认为,无论前因何起,仲家败落,就是乐无涯一手所为。真要细细追究,仲家夫妇的死,也不能说与乐无涯全无关联。留这么个隐患在身边,闻人约担心哪天仲国泰午夜梦回,梦到爹娘,拧了心思,偷偷跑来把乐无涯掐死。乐无涯的想法是:他若起了这等心思,我正好送佛上西天,趁着年节刚过,赏他份阖家团圆。闻人约仍然坚持认为,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若这仲国泰是个心智坚忍之人,蛰伏在他身边,只为着伺机狠咬他一口呢?随着乐无涯与闻人约与日俱熟,乐无涯发现,此人当真是个无可转圜的天生犟种,天生是个干御史的好材料。乐无涯不想同他再起争执。万一又把人气跑了,他还真要去南亭书院哄他。乐无涯索性另起话题,撒娇道:“饿了。想吃苏式的热汤面。”他的心思昭然若揭,闻人约简直要被他气笑了,但还是据实答道:“没有高汤。”乐无涯:“昨天还有点剩鸡汤呢。”闻人约叹了一声,挽起袖子,进了厨房,投喂他的顾兄。……仲国泰听乐无涯说完以上种种,默然无声。几日前,他回到南亭时,瘦得几乎脱了相,等他剃去一部凌乱的胡子,活脱脱成了个小仲俊雄。太平时节,仲俊雄训斥他时,总说“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一个畜生”。仲国泰自己也暗暗怀疑过,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们亲生的。现今他不怀疑了。他与父亲,连心也连相,是血脉相连的亲生父子。在外流浪许久,仲国泰至少学会了不说蠢话。想不通的事情,放在心里慢慢想,总能抿出个头绪来。他垂着眼睛,神情半明半昧。思索片刻后,他问乐无涯:“这么说,没得审了?”乐无涯热热闹闹地吃着面,把嘴唇烫得通红:“正道反正是走不通了。”“那邪道呢?”乐无涯还是摇头。闻言,仲国泰登时几步抢到阶下,赤红了眼睛,直直瞪着他:“闻人约,你答应过我什么?!”他的眼里闪过凶光,叠加着走投无路的泪光:“你怎么对付我家的,你倒是对付回去啊?”乐无涯不惧怕他的疾言厉色。他将筷子横放在面碗上,审视了他片刻,轻伶伶地一笑:“我倒是想依葫芦画瓢呢。可侯家的两个儿子个个争气,都在南亭书院读书;师家的闺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人家又没养出烂葫芦来,不好下手啊。”仲国泰犹如凭空挨了个窝心脚,不吭声了。他锋芒全无地垂下头,大狗似的蹲在了台阶下。想哭,没眼泪。他埋头半晌,又从膝盖里抬起头来,嗓音嘶哑得不成样子:“罗织罪名,还不简单么?要是有不服的,打一顿板子,上一顿夹棍,没有不招的!”乐无涯:“哟,仲少爷出了一趟远门,着实涨了不少见识。”仲国泰负气道:“你们当官的,不都这样吗?”乐无涯单臂压在膝上,身体微微前倾,好整以暇地问:“我的官声,是我在南亭一步步苦心经营出来的。你们仲家父子,爹要我的命,儿子要我的名声,个顶个的不跟我客气,真是好大的一张脸啊。”仲国泰呆在原地,被他怼得张口结舌,心如火焚。闻人约在旁看到现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颇不赞成乐无涯将仲国泰留在身边的冒险之举,可见仲国泰犹如困兽,几乎要发疯的模样,他亦是不忍。于是,他走上前去端乐无涯的汤碗。在路过仲国泰身边时,闻人约轻声提示道:“他有主意。”仲国泰将这四个字在心里颠来倒去地琢磨一会儿,原本灰败的脸色顿时放出了光明。他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太爷,我知错了,求您给我指条明路吧!”乐无涯瞪了闻人约一眼。他正要磨砺这小子呢。筋骨倒是结实了,可脑子总转不过来怎么行?闻人约微微的笑了笑,受了他这一瞪。乐无涯身上暖了,肚子饱了,精神百倍地站起身来,将那条愈合的腿在地上跺了跺,步伐轻快地来到了仲国泰面前,端起他的下巴,研究起他的面容来。仲国泰刚才还凶悍地瞪着他,恨不得从他身上撕下一块肉来,如今骤然和他对视了,却一下子失却了勇气。
他看他,还是天人之姿。但此时的仲国泰,早已没了那不正经的亵玩之心。眼前人,是真正的天上人,只要肯发一发慈心,就能给他一个公道。“正道不行,邪道不行……”仲国泰轻声道,“那您想走哪条道?”乐无涯轻巧一笑:“鬼道咯。”……转眼,年关已过,乐无涯再次将南亭诸位里老人集合在一起。但这回,不去衙门,改去拜城隍。南亭县的城隍庙位于城西。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城隍供奉的具体是哪一路神仙,就连许多南亭耆老也说不清。当年大虞与景族交战时,有不少百姓都来南亭城隍庙参拜,祈求战事顺利,儿郎能够平安归家。后来,大虞律规定,但凡县令走马上任,必定要先参拜当地城隍。新年新气象,太爷想来拜一拜城隍,祈求新的一年再加官进爵,县中太平,也是合乎情理的。侯鹏与师良元穿上一身新衣,老老实实地赴了会。他们私底下谋算过太爷,面对太爷,总有那么点似有若无的心虚,总担心在他面前露了行迹。至于仲俊雄……那人已经不在他们心里了。他们之所以如此坦然,就是笃定,但凡仲俊雄聪明一点,就算他人之将死,也只会把那桩秘密带进坟里去。仲俊雄是没有任何证据来指证他们下毒害人的。相反,他自己一身的肮脏,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白。只要他敢唆使家人回到南亭告状,必然绕不开他谋害太爷的那桩烂事。换言之,他只能自认倒霉,死了也白死。至于前段时日,有个面目狼藉、瘦骨支离的乞丐,推着板车,带着两具尸身穿街过巷地去敲鼓鸣冤,侯、师二人仅仅是有所耳闻,压根儿没往心上放。理由很简单。仲俊雄勉强能算得上一个狠人,但仲世侄是他们亲眼看着长大的,知道此人废物得一骑绝尘。就算爹死了,他大概也只会哭哭啼啼地找娘亲要奶吃。若是沦落成乞丐,他第一日就该自杀了。此人诚不足虑也。二人春风得意地进了城隍庙,只在心中暗道,这日子选得邪性,怎么非要在这么个阴云蔽顶、风雨欲来的日子拜城隍?庙内光景与庙外不同,烛火光明,香火鼎盛。披挂华彩的神偶坐在袅袅的香烛雾气中,有金刚怒目,也有持棒罗汉。稻、黍、稷、麦、菽五谷早已摆设就位。进庙之前,尚有人切切察察,议论不休,可迈入正殿后,众人受这肃穆气氛所染,不敢造次,纷纷闭口不言,在预先摆好的蒲团上跪下,一一拈香祈祷。在四下静谧之时,窗外风声愈狂。城隍庙的一扇窗户大抵是年久失修了,有些缝隙,那窗户便被风牵扯着,不住发出细微的撞击响动。叩叩,叩叩。似是有人在叩门敲窗,又似是有人在外踱步逡巡。乐无涯向来是个能说能笑的性子,今日却安静得异常。各位里老人私下里递了几个眼神,不知道太爷又要闹什么玄虚。乐无涯遵照祭祀要求,一步不错地执行过后,立起身来,朝向了众人。这一年光景下来,他们与小太爷时常相见,没觉出他的样貌有何大变。变是肯定变了,但具体变了哪里,他们说不大清楚,只当他是大器晚成,慢慢长开了。可他这一转身,许多人瞧出了异常来。他不必着红妆,便是色彩鲜明、鲜花着锦的一个人。唇是鲜红,脸是雪白,烛火映衬下,眼睛落在鼻凹和睫毛交织的阴影里,看不清神情,只能看出一个“鬼气森森”。“诸位。”在里老人们不由得屏息凝神后,乐无涯开了口。“祭祀城隍,乃古之礼法,求的是保护城池,天下太平。自大虞圣祖始,更是将‘礼敬城隍’一事写入了《大虞礼法》中。城隍不仅护佑一方平安,更是司法之神,主持着一方百姓的天公地道。”“在此之前,我虽是礼敬,心中却并不相信。”说着,乐无涯将单手覆盖在胸口上,郑重道:“在明恪看来,若是百姓们将希望寄托在木偶泥佛之上,只能说明,明恪为官无能,叫百姓求告无门,只能去祈天求地。”侯鹏一笑,奉承道:“太爷真是太过自谦了。”乐无涯对他轻轻一颔首,随即道:“可自从前夜偶得一梦,见到一位意料之外的故人后,我便有些怀疑,这世上是否真有鬼神?”乐无涯这一句话,勾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兴趣。是谁?乐无涯娓娓道:“那人身入我梦,身形有异,身躯枯槁,偏偏肚大如箩,只能用手环抱着;眼里流泪,口角流涎,张着嘴要对我说什么。但他究竟说了什么,我在梦中,始终是听不清。”窗外风声渐急,宛如细细的涕泣声,如怨如诉,如泣如慕。众人身在城隍庙,在群像环伺下,听乐无涯说鬼道怪,无不悚然。乐无涯眼珠微微一转,有紫色的精芒闪过:“我想,我一人之力,怕是不能辨其冤,听其屈,便将此人旧识召唤来此,并借城隍老爷庙堂,好细问一问,他究竟想要对我说些什么。”旧识?侯鹏和师良元对视一眼,心中俱是浮现出不妙的预感。有旁人替他们问出了心中疑窦:“太爷说的那人,我们也识得?”乐无涯并不应声,而是放开声音,道:“我们都已到齐,城隍老爷也在此处。……你来了吗?”他话音刚落,外面风声大起。那失修的窗户骤然被烈烈大风撞开,寒风倒灌,将庙中烛火尽数吹灭。桌椅咯吱咯吱地发出细响,仿佛是那门外踱步的鬼魂撞窗而入,有脚步声在四面八方响起。在座诸位心下惊骇,即使并不大呼小叫地宣之于口,也暗暗地各自抚胸心悸。乐无涯声音仍然稳当:“各位勿慌。何青松,叫人重新将烛火点好。”守在两侧的衙役们齐应一声。有衙役镇守,众人心绪渐安。然而,侯鹏想起一名故人,顿觉如芒刺背,难忍心虚,眼珠四下乱转,生怕真的来了什么人,从后搭上他的肩膀,问一句,“侯兄,今日带的什么酒?”在他胡思乱想之际,灯火从他身侧最先亮起。出于本能,他向灯火亮起处看去。他猛然一愣。原本立在他身侧的那尊伏虎罗汉,不知何时换了人。一个枯槁的仲俊雄,盘腿坐在那泥质的法座之上,目眦欲裂地直瞪着他!侯鹏喉咙里“嗝喽”响了一声,惊颜如土,一屁股跌坐在地。点火的何青松被他吓了一跳,手一抖,刚点亮的火折子随之落在了地上。烛芯并未点燃,四下里再次陷入了一片寂然的死黑。侯鹏叫不出声来,仿佛被什么人扼住了咽喉。而乐无涯突然笑了一声,对着虚空郑重道:“仲俊雄,仲老板。”“……你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