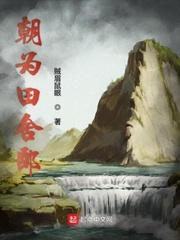墨澜小说>哥哥,恋人 > 妹妹281 旧照片里的龙翔(第1页)
妹妹281 旧照片里的龙翔(第1页)
因为梦七月份工作神忙,从今天起每日一更到全文完,但其实后面每章字数都比之前多,所以大家不亏的。(_)
---------
要不要留下来,我挣扎了很久。
同事们的谣言与关心,还有不知道池隆见会给我看什么的好奇,两向拉扯,最后还是好奇心获胜。
我隐约感觉他给我看的东西也许跟那漫画有关,说不定,也跟我有关。这是一种很没有道理的感觉,却那么强烈,迫使我很想要赌一下。
翻开anda记录今天的总结,看着右上角的日期,恍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出来一年多了。感恩节,圣诞节,元旦,春节,那么快就都过去了。日歷上那些曾经以为对自己很重要很重要的节日,那些我以为永远不会忘记的快乐与痛苦的纪念日,都在我一心一意围着小羽的忙碌中从我身边匆匆溜走,我都没来得及缅怀。
圣诞节强子送了我一块表,新年那天同事们跑出去倒数许愿,除夕夜城市电视有转播春晚,正月十五yu也有买元宵。生活一直在顺理成章地继续,而我却什么也看不到。除了工作,回家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站在熟睡的小羽的床边发呆。
餵奶,换尿布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我总是搞不好,但我一直努力在学,只要我在家就不借他人手。经过好几次换尿布的『突发事件』,我突然明白了老一辈人说的『一把屎一把尿』是甚么意思。
当了妈之后,孩子的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就算他毫无预警吐我一身,拉我一手,都不会觉得噁心或着生气。每天扒着尿布研究宝宝的便便。绿了,稀了,就紧张兮兮怕他着凉,怕他喝配方奶消化不良,怕他肠胃感冒。奶喝得多了怕他撑,喝得少了怕他饿。他打个喷嚏我就开始担心自己照顾不好他。
那个曾经幼稚无知的我,伴随着那些记忆,距离自己越来越远。如今坐在这里,回想自己一个人在老房子里的平安夜,竟像是上个世纪的事,那么久远。
我想,说不定也许我已经可以放下了。我的坏记性,在这种时候,总也算是种优点。
下班前我给强子打了个电话,让他晚半个小时带小羽过来接我。
我想起了米奇楚,还有那次有惊无险的经歷,只差那么一点点就无法挽回。现在的我不能有一丝差错,因为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人。
半个小时,看点儿东西应该够了吧。
为了避开同事间不必要的闲话,下班之后我和平时一样先出了门赶公车,等到同事都差不多走光了,才又返回了工作室。其间浪费掉了十分鐘。
旧公寓走廊里骯脏昏暗,有一点像老电影里的镜头,带着垂暮的气息,安静的,几乎静止。空气中有淡淡的大麻味道,靴子踩在掉光了毛的地毯上,下面腐朽的木头被压迫时发出尖锐的呻吟,墻上有一串不知是谁甩上去的番茄酱的暗红斑点,心跳莫名变得急速。
我略加快了脚步,推开门框上贴着红色变形福字的门。那是池隆见随手画的,很怪,张牙舞爪的,一点儿幸福的感觉都没有。我一把按在了福字的那个『口』上面,像被咬了一样猛地收回手。
进门依旧一片昏暗,只有池隆见的专署创作室里开着灯。那是用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一块毛玻璃屏风隔开的空间,毛玻璃上贴着厚厚的好几层画稿,完全不透光。
黑暗中的空气显得凝重,飘着浓浓的菸草味道,让人倍感压抑。我突然有点后悔,这样单独留下来,真的是个明智的决定么?
我轻手轻脚地在黑暗中摸到能看见创作室的地方。池隆见坐在工作台后面,工作灯伸着长长的支架,照着他手里拿着的一张白纸。他看得很投入,拿菸的手撑着额头,挡住了脸,好久都没有动。
菸灰烧得太长,终于撑不住掉了下来。他回过神,抬头向我看过来。我本能地想跑,但腿脚的反应还是慢了半拍,已经被他看到,干脆就没动。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他把手里的白纸放在工作台上,反射着灯光,影影绰绰一片灰白。
我这才发现,那是一张照片,脉搏不由得悸动起来,我感觉似乎有颗种子在土里蠢蠢欲动,快要破土而出。
「进来吧。」他冲我招招手,「放心,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池隆见倒是直接,这么直接,让我的担心都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觉。
我绕过屏风,站在那里看他把堆在椅子上的画册搬到地上。他弯着腰,有些吃力,话讲得断续模糊:「你就像是我的女儿。我能对自己的女儿做什么呢?」
我的大脑很没出息地嗡响了一声。我在心里暗暗骂自己,胡思乱想什么呢。他见不着女儿,我没有爹,也不能就这样凑一起吧。
我站在原地大口的吸了几口气,这才一步步走向他。
他站起身,把菸头摁在菸灰缸里,像平时一样伸手摸摸我的头,嘴里喃喃地叫着我的名字,带着疑惑与不确定:「龙珠……你的中文名字叫龙珠?」
我点点头。
他也点点头,皱起了眉头,继续喃喃地重復这两个字:「龙……珠……龙……珠……」
我仰头看着他杂乱的胡子中间轻轻蠕动的嘴唇,听见自己的小心心在胸膛里慌了神一样地乱跳。我没出息的脑子里又开始闪现无数的念头,杂乱无章,拎不出一点头绪。
我的天,不会真的这么雷吧。
池隆见终于放过我已经一个头两个大的脑袋,拿起桌上的照片递给我。我都不记得自己怎么接过来的。在我的大脑恢復意识之前,照片已经在我手里了。
那是一张集体照,在一群人里,我一眼就看到了龙翔。心脏一瞬间揪成一团,疼痛酸涩地堵在胸口,几乎喘不过气。
还说自己放下了,放下了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