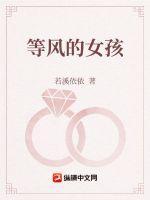墨澜小说>游剑江湖(原名:弹铗歌) > 第246章(第2页)
第246章(第2页)
武端兄妹正在朝着山上跑,郝侃从上面滚下来,恰好滚到他们的面前,就一个“鲤鱼打挺”,翻个身跳起来了。
武端吃了一惊,蓦地喝道:“好呀,原来是你这狗贼!”说时迟,那时快,兄妹俩不约而同的拔剑出鞘,立即向郝侃刺去。
郝侃虽然受了重伤,本领毕竟还是要比他们兄妹高强,他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狞笑说道:“你这两个娃娃送上门来,我这个做师叔的只好不客气了。”原来他在高处看下,早已看见武端兄妹后面的刘抗,情知难以逃胞,是以恶念陡生,便要把他们兄妹随便抓着一个,作为人质。
双方喝骂声中,郝侃腾的飞脚一踢,武庄手中的长剑给他踢落,但他的脚跟却也给剑尖划开了一道伤口。
说时迟,那时快,武端唰的一剑,已是指到他的咽喉,郝侃突然张口一咬,咬着了剑尖。武端用力一插,竟是不能再进分毫。
刘抗刚刚转过山坳,看见了这个情景,也是不禁吓得呆了。施救不及,一呆之后,只好连忙叫道:“弃剑,弃剑!”
武端到底是欠缺临阵的经验,他想不到郝侃有此一招,一给他咬着了剑尖,只知道要用力把长剑插进去,却未想到要弃剑逃跑。
刘抗出声指点,已是迟了一步。郝侃双臂一伸,倏的就把武端拦腰抱住!
武庄拾起长剑,一招‘明驼骏足”刺郝侃下盘,郝侃滴溜溜一个转身,把武端推向前面,喝道:“刺罢!”
武端叫道:“缪师叔快未!妹妹,不必顾我,快刺!”他给赦侃拦腰抱住,身子不能动弹,一个“肘捶”,就撞郝侃心口,郝侃怒道:“你找死么?”他的两排牙齿仍然咬着武端的剑尖,从牙缝里漏出声音,就好像患了重伤风的人说话一般。
本来郝侃此时双手不敢放松,武庄要刺他一剑,那是易如反掌。但哥哥被郝侃抱住当作盾牌,她的剑法纵然精妙,也悄万一失手,误伤了哥哥,如何敢鲁莽从事?
武庄正自无计可施,忽见一条人影,凌空扑下,扑在郝侃身上,赦侃发出一声裂人心肺的呼叫,武端的长剑已是拔了出来。郝侃抱着他一同倒地!
与此同时,那条人影也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跌了下来,正是那个卖艺的姑娘。
原来那个卖艺的姑娘在武端遇险的时候,立即爬上悬崖,攀着一条山藤,像荡秋千似的悄无声的凌空飞渡,荡将过去,扑到郝侃身上。这种“飞索横空”的功夫,正是她的拿手本领。郝侃背向着她,根本没有发觉。
她一扑到郝侃身上,就狠狠的朝郝侃的后颈窝一咬,这是人身要害之处,郝侃给她狠狠的一咬比受利剑所伤更惨,当真是痛彻心肺,不由得杀猪般的嚎叫起来。
这么一来,他咬着剑尖的牙齿自是不能不松开了。武端用力一插,剑尖透过他的咽喉!
他的内功确也了得,临死之际,居然还能牢牢的抱着武端一同跌倒。那卖艺的少女,也给震得从半空中跌下来,那条细长的山藤,早已断了。
卖艺的汉子忙把女儿接下。武庄也连忙上前,给郝侃补上一剑。郝侃劲力一消,双臂软绵绵的松开,武端这才能够脱身,伸了伸舌头,说道:“好险!”
武庄说道:“哥哥,人家为你冒的险更大呢!”武端霍然一省,跑过去向那少女道谢。
只见那少女面如金纸,她的父亲正在给她推血过宫。武端十分过意不去,说道:“姑娘,你舍命救我,我还未曾知道你的名字呢,你怎么样了?”
卖艺那汉子说道:“我姓程,名叫新彦,小女名叫玉珠。武公子不用担心,小女虽然受了郝侃这厮内力所震,幸好并未重伤。她歇一歇就会恢复如初的了。”
说话之间,从山顶下来的缪长风和从山坡上来的刘抗都已到了。
程新彦说道:“刘老弟,我来迟了一步,几乎累了武公子。这位就是缪长风缪大侠吗,幸会,幸会,幸会!”
缪长风叹道:“我刚才一念之慈,没有杀掉郝侃,要不是得令媛救我这师侄,我的罪过就是百死莫赎了。”
武端兄妹忽地朝天一拜,随即把郝侃的头颅砍下来,哀声说道:“爹爹、妈妈,孩儿不孝,今日才能为你们杀掉一个仇人。”跟着又向程玉珠跪下磕头。
程玉珠会得满面通红,她不便扶起武端,只好也跪下来还礼。
缪长风与刘抗相视而笑,心里不约而同的都有一个念头:“这位程姑娘和武端倒是很好的一对,看来他们似乎也都有点意思了。”当下缪长风扶起武端,刘抗扶起武庄。缪长风笑道:“想不到你们这些少年人比我们老一辈的还要多礼。”另一边程新彦扶起了女儿,笑道:“珠儿,你不是有话要和武公子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