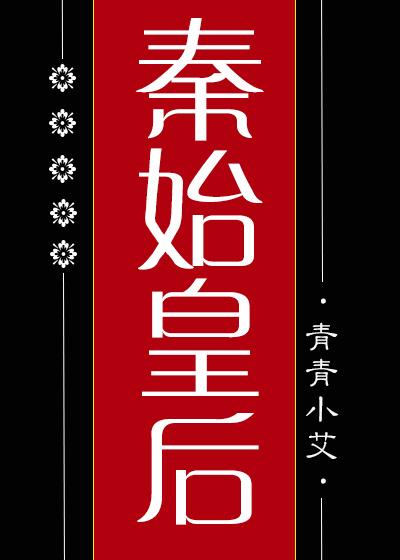墨澜小说>幻剑灵旗 > 第91章(第2页)
第91章(第2页)
穆娟娟淡淡说道:“你若不是死到临头,恐怕也不会认我这个姨妈吧?”
宇文浩寒透心头,蓦地想起:“妈妈说过,齐勒铭曾经服下她的一年之内有效的酥骨散,而且后来他的琵琶骨亦已给他这姘头捏碎了的。即使酥骨散有解药,但琵琶骨碎了是难补好的,琵琶骨一碎,气力就使不出来,我怕他作甚?”
这么一想,他刚才被齐勒铭用狮子吼功吓破的胆子又大起来了。他自作聪明的猜想:琵琶骨碎了,内功还可以练,但出手无力,多好的内功也不能发挥。而齐勒铭之所以迟迟尚不出手,目的恐怕就是要用狮子吼功来吓走他。
生死关头,与其束手待毙,何如冒险一搏?更何况他以为齐勒铭是真的已经被废了武功?
“饶命!”他口中大叫。突然在装作下跪之际,一剑向齐勒铭小腹刺去。
只听得一声惨叫,齐勒铭手中无剑,但中剑倒下去的却是宇文浩。
齐勒铭只是使了一招借力打力的巧招,把他的剑反拨回去,让他用自己的剑穿了自己的琵琶骨。
“看在你姨妈的份上。饶你不死。但你若想恢复武功,那就得要看你以后怎样做人了。你若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说不定过了三十年,我会教你怎样在琵琶骨碎了之后重新练功的法子。”
齐勒铭一面说一面向那座冰台走去,冰台下面,上官飞凤和卫天元还在和对手激战之中。
南宫旭和武鹰扬看见齐勒铭来到,不是心里不慌,但一来是欲罢不能,旌鼓相当的高手搏斗,除非双方同时停止,否则谁先罢手就只有谁先吃亏;二来他们料想齐勒铭也不会不顾身份,在一对一的单打浊斗中插上一脚。
谁知齐勒铭不但是插进一只脚,而且是整个身子都“插进”去了。
武鹰扬和卫天元是正在比拼掌力的,要分开他们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齐勒铭却背负着双手,硬生生就插进他们中间,把他们分开了。
只听得“蓬、蓬”两声,武、卫二人都是双掌打在他的身上,也同时给他反震出三丈开外。卫天元靠着一条冰柱,武鹰扬背后是空地,直打了三个盘旋,方始稳住身形。
齐勒铭神色自如,说道:“我是一帆同仁,我既然来到,我的事就用不着别人代劳,谁都不许再打下去。”
他的确是并没有偏帮哪一方,只是以他自己的身体硬接了武、卫两人的掌力。
说话之间,他又已来到了上官飞凤的身边,上官飞凤的一把长剑和南宫旭的一对判官笔也正在打得难解难分。
齐勒铭眉头一皱,说道:“我给你们定出输赢吧!”突然衣袖一挥,南宫旭的判官笔被卷了过来,飞上半空;上官飞凤倒跃出去,长剑居然并未脱手。
齐勒铭一看袖子,说道:“我这一卷力道对双方都是一样的,上官姑娘的剑没有给我卷去,但南宫香主的判官笔却刺破了我的衣袖。依我看是都没输赢,你们服不服气?”原来上官飞凤胜在乖巧,她虽然来不及收剑,但一觉袖风拂面,剑锋便即闪电般的贴着袖子“滑”过去,而她的身子也像游鱼般的滑开了。不过,南宫旭的判官笔能够刺破齐勒铭的衣袖,功力却是胜她一筹。
上官飞凤道:“齐叔叔,你的剑法我一向是心眼口服的,有你来到,自是无须我献拙了。”其实齐勒铭刚才显露的并非剑法,她故意这样说,乃是来个“伏笔”,要看“下文”的意思。
南宫旭则没说话。
齐勒铭果然哈哈一笑,说道:“你们不服也得眼,因为是我自己要打下去,你们不罢手,我就找不着对手了。”
齐勒铭喝道:“齐家和白驼山的梁子由我和你们作个了断,两位大香主,你们已经打了一场,我不想占你们的便宜,你们并肩子上吧!”
南宫旭与武鹰扬面面相觑,甫宫旭连跌落的判官笔都不敢去拾,哪里还敢上前?武鹰扬更如斗败的公鸡似的,垂头丧气。
齐勒铭冷笑道:“你们的气焰哪里去了?刚才还那么嚣张,向我的爹爹挑战,如今我替爹爹应战,你们因何还不出手?难道你认为我不配做你们的对手吗?”
南宫旭道:“齐大侠、我不是你的敌手。你若要替令尊出气,剁剐随你的便!”说得似乎颇有“气概”,其实是存着侥幸的心理,博一博齐勒铭或许下会杀他。因为他业已放弃抵抗,连兵刃也任凭它委弃于地,江湖上不成文的规矩,对方若然讲究“好汉行径”的话,是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的。
齐勒铭却仍然冷笑道:“你们不敢和我动手,却有胆欺负我的爹爹!是谁给你们这个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