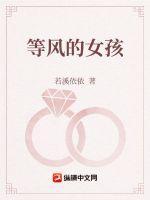墨澜小说>快穿之霸道男主爱上我 > 第91章(第1页)
第91章(第1页)
“爹,你说他是什么人呀?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爹不知道,总归不是普通人,待他伤势好些,就让他离开吧,免得带来麻烦。”
“爹……”
黑暗中最后一丝光亮渐渐衰败,天边升起的太阳光洒在那身泛着金光的龙袍上,将人的野心一览无余的展现出来。
“镇南王皇三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舆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中外,咸史闻知。”
身着丧服的太监手持皇帝遗诏在朝堂上宣读。
萧长渊负手站在他旁边,神情悲戚。
朝下议论纷纷,从皇上驾崩,到平西王和定北王谋反,再到现在的皇上遗诏,这一切都太紧罗密布,让人忍不住生疑。
林启书藏在袖中的手紧攥,终于还是没忍住,上前一步:“敢问镇南王,这诏书是先帝于何时所写,写时身旁可有人?”
这话再直白一点就是直接问萧长渊,你这个遗诏是不是作假了。
萧长渊转身看向林启书,别有深意的说了一句:“原来是前定北王妃的父亲啊……”
“前”这个字眼他咬的很紧,林启书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萧长渊微微一笑,仿佛正吐着信子的蛇,他伸手指向身边的太监,开口道:“父皇写下诏书的时候只有元庆和他在场,元庆已在父皇驾崩后随他去了,而他是元庆亲传的徒弟,林相可还有疑问?”
“有!”林启书抬头直视萧长渊,“敢问镇南王,定北王谋反可有证据?”
萧长渊挑了挑眉,“还要什么证据?那么多人都看见他和平西王在城外,还带着军队,父皇还未驾崩,平西王就从西北回城,不是要逼宫是什么?”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林启书从始至终就不相信他所说的一句话,可是他儿生死不明,定北王坠落悬崖,这偌大的朝堂难道真的就让萧长渊只手遮天了吗?
“萧长渊!”
大殿外传来一声厉喝,众官员回头望去。
只见太后身着丧服,面容冰冷的一步步走到大殿上,凌厉的目光直逼向萧长渊。
萧长渊眉头微皱,“母后缘何会来这大殿上?”
“别叫本宫母后,本宫没有你这种谋害皇上的儿子!”
太后这句话引起一片哗然之声。
萧长渊面色不变,“儿臣知道父皇驾崩,平西王被捕,母后悲痛欲绝,但是母后也不必如此编排儿臣。”
“编排?”太后冷笑一声,抬起手,掌心上放着一个瓷瓶,“这是本宫在先皇寝宫的香炉里找到的香料,你敢说你不是用这种东西害的先皇缠绵病榻?!”
“先皇不过知天命的年岁,正直壮年,为何会无故病倒?!为何?!”
萧长渊用舌尖抵了抵脸侧,唇边勾起一抹笑,皇帝寝宫的一切东西都被他毁了,没想到皇后居然能找到这个。
他抬手,目光渐冷:“母后伤心过度糊涂了,身边的人也不看好,来人,送太后回凤朝宫!”
殿外立马走出来两个侍卫,竟然是要强行带走皇后。
当朝的老臣见了立马痛斥:“放肆!你们竟敢对太后无礼!”
侍卫的动作停顿了一下,看向大殿上方的萧长渊。
萧长渊没作反应,侍卫们会意,欲继续带太后走,却被太后用力推开,“萧长渊!这皇位不是你的!就算你杀了我也不会是你的!”
说罢,她便自行走出宫门。
她曾是皇后,现在是太后,她的丈夫死了,儿子被囚,她不能连最后的尊严也被萧长渊踩在脚下!
大殿上的萧长渊脸色铁青,背在身后的手攥出青筋,他倒是没想到那个虚荣的女人胆子会这样大,敢来金銮殿闹这一出。
“镇南王,不觉得你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吗?!”一位老臣责问道。
鱼相从侧方走出,“太后痛心疾首之下说出来的话怎么能信?更何况她的儿子还是叛臣之首!”
“鱼相你!”那人没想到鱼相会帮着萧长渊说话,“你竟然帮着这个乱臣贼子说话!你忘了先皇在世是如何器重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