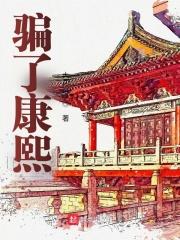墨澜小说>驸马,公主把你的小妾拐跑了 > 第139章(第1页)
第139章(第1页)
季青叹了口气说道:“我知道你担心傅姑娘,但你们如今身上都有伤,两个病人相见了只会彼此伤心,并不是什么好事,等身体好了再见吧,你若是真放心不下她,让喜儿帮你传话罢,你放心,你说什么都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季青说完阮雨棠的脸便红了起来,她虽然知道季青早就看出了自己和何为常的关系,却没想到季青能说出这么直白的话来。
季青虽将话说了出来,心里却还是觉得有一股气堵在那里,怎么也无法消解。她来到后花园散心,初冬的园子里只有些凌乱的树枝,连一点绿意都很少见到了。她站在水边,湖里的金鱼看见她的影子都纷纷围拢了上来。当年她也是这样和表姐站在水池边喂金鱼,一勺子鱼食撒下去,金鱼纷纷上前争抢。此时的她刚刚得知了兰妃的死讯,她原本是不准备和表姐提起钟宁儿的,可是在来的路上撞见七皇子因为顶撞皇帝被侍卫压了下去,到底还是忍不住感慨道:“可怜了两位皇子,连亲生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着,皇帝怎么也不体恤七皇子的思母之心,这样苛责他。”
陆离挑起一勺鱼食洒进水里,看着水里抢食的鱼,说了一句:“重病之人形容枯槁颜色衰败,连句话都说不出来,见了只平添几分伤感罢了,其实倒不如不见的好。”
季青听了表姐的话,便低下头默不作声,她突然意识到表姐说的病重之人是谁,心里一惊打翻了手上的鱼食,整罐鱼食全洒进了水了,成群的金鱼涌了过来在水里翻腾着抢食。
【??作者有话说】
若是有幸能和相爱之人在一起,莫辜负了青春好时光。
120?封城
◎何为常只能在心底叹了口气,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还能没能制止阮雨棠掉下眼泪。◎
陆离捡起了鱼食罐塞回季青的手上,说道:“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冒冒失失的。”
季青抓紧了罐子,问道:“表姐你去看她,皇帝知道吗?”
陆离依旧悠闲的撒着鱼食,漫不经心的回道:“皇上自然不知道。”“她说了什么吗?”季青不知道应该如何问,可是她又不甘心什么都不知道。“将死之人,气若游丝,什么话都说不出了。”陆离还是淡淡的口吻,像是说着偶然听来的闲言。
季青站在池边,看着满池抢食的小鱼,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当年问错了问题,比起宁钟儿如何,更应该问的是陆离为何要避着皇帝去看将死的宁钟儿。她转过头轻声问道:“表姐,你为何要去见她?”可是她的身旁空无一人,只有冷风飒飒从枯瘦的枝干间吹过。
入夜后窗外的风更大了些,天气越来越冷,屋子里已经生起了炭炉。喜儿拨了拨炭炉里面的火,将炭炉搬到阮雨棠的床边。阮雨棠看了看为了防风用纸糊得严严实实的窗户,有些担心的说道:“你把窗户打开留条缝吧,在屋子里烧炭取暖还是要多留意些。”喜儿笑着说道:“公主放心,我已经将另一个窗户推开了少许,这扇正对着床的窗户怎么能开呢。”阮雨棠也笑了。
腿上了伤一直都在疼,阮雨棠没办法入睡。她歪头看见喜儿坐在旁边又开始打瞌睡,便让她先去睡,喜儿却怎么也不肯,直到阮雨棠佯装生气了,喜儿才说自己可以在床边的踏上小憩,让阮雨棠有事就叫自己。阮雨棠想着何为常如今怎么样了,是不是也被疼得睡不着。其实何为常自从那天昏倒之后直到现在也没醒过来,太医们的药一直喂下去,却一点起色也没有。季青请了好几个太医来瞧,几个太医开的方子煎了药轮番喂了下去,却一点也不见效。
阮雨棠身上的伤本就不严重,第二天就结了痂。季青见她已经能起身,便让下人抬着软轿送她去见何为常,与其让阮雨棠自己下床拖着病体到处走,倒不如自己找人抬她去。
房间里静悄悄的,下人将阮雨棠抬到床边就退了出去。透过床帘阮雨棠只能隐隐看见一个人躺在床上。她挣扎着站了起来一步一顿走上前,伸手掀开了床帘。何为常安静的趴在床上,头朝着床内看不清脸。阮雨棠坐到床边,伸手先摸了摸何为常放在被子外面的手,还是如何往常一般的温暖。她握着这只手,就像往常习惯性的那样摇了摇,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这双手依旧是熟悉的温度,这令她安心了不少。
她轻轻地唤了一声;“为为。”
何为常就像以往一样,回了一个字;“嗯。”
阮雨棠吃惊的伏到何为常肩上,伸手拨开散落在何为常脸上的头发去看她的脸。何为常赶紧哎呦了一声,说道:“小祖宗,我背上全是伤口,哪禁得住你这么压。”阮雨棠赶紧起身,见何为常想翻身却又翻不过来的样子,赶紧过去扶住了她,却又怕压到她的伤口,只敢抓着她的手腕。何为常又叹了口气说道:“胳膊要被你拽掉了。”阮雨棠想要放手又怕她跌到床上,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起来。何为常笑着说:“你凑近些,我扶住你的肩膀借力不就好了。”阮雨棠依言凑上前,何为常却张开双臂将她搂在怀里,感慨了一声:“我晕倒前一直再想醒了之后第一眼看见的会是谁,要是一睁眼发现自己被扒光一堆人围着我涂药,那该多尴尬,还好。”何为常的话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她感觉阮雨棠的眼泪滴到了自己的脖子上,冰冰凉的眼泪,润湿了她的衣襟。何为常只能在心底叹了口气,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还能没能制止阮雨棠掉下眼泪。
风继续吹着,吹得池塘边的枯枝飒飒作响。
香云低头看着池中被风吹得不断掀起涟漪的水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四周都太安静了,安静到听风声由远及近的吹过来,安静到能听见水中鲤鱼吐泡泡的声音。院门突然被人推开,香云回头看见郑丰慌慌张张的闯了进来,香云还没来得及问为何他会闯进来,郑丰已经上前拽住了她的胳膊说道:“姑娘,王爷让我送你离开这里。”
时安泰跟着荣王前前后后的忙活起来,荣王多年来都不曾过问朝堂之事,如今何人担任何种官职并不十分清楚。所幸陈檀很快从迷茫中回转过来,帮着指点传人问话。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堪堪将人员安排了下去。陈檀依旧回港口去,时安泰自行回王府。
他已然让郑丰带香云离开了善兴,至于去什么地方他一时也做不了决定,只让郑丰走得越远越好,远到连他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于管事年迈之人昨夜忙了一夜,今天没到中午就晕了过去,时安泰让人赶紧送回了王府,现在只怕还在睡着。时安泰随着习惯走到了院子门前,他想香云此刻应该已经不在院子里了,郑丰是会带着她往东走还是往西走呢,往东走到最后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往西走最后是黄沙漫漫的边关,香云会往什么地方走呢?时安泰这么想着,一边推开了院门,却惊讶的发现屋子里和往常一样点了灯,那一盏暖黄的灯火透过窗户在将暗未暗的黄昏中看起来有些不真切。时安泰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他快步过去打开了房门,却没有在书桌后看见熟悉的人。时安泰靠在门框上,忍不住嘲笑自己,明明是自己让香云走的,此时为什么还希望她会留在这里。香云却从灯光微弱的角落里站起了身,那里的灯光太昏暗了,昏暗到时安泰一进来根本没注意到墙角还坐着一个人。香云从光照不到的角落里走了出来,走到灯光照耀的地方,走到时安泰能够看见的地方。
时安泰看着她忍不住扬起了嘴角,转眼却又放下嘴角,焦急地问道:“我不是让你跟郑丰走吗,你怎么没走?”
香云走到他的面前,依偎着他缓缓坐到了门槛上,将头贴在他的膝盖处问道:“郑丰说王爷是为了我的安危,才准备将我送出善兴,可是如果王爷身边都不安全,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呢。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待在这里,待在你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