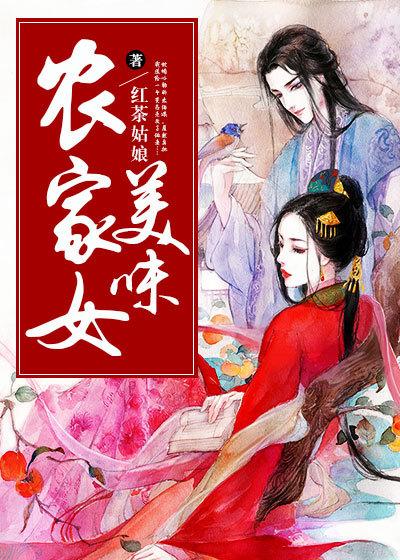墨澜小说>[红楼]护国公主 > 47 第四十七章 三合一(第2页)
47 第四十七章 三合一(第2页)
赌她其实也不甘心就这样放过仇人。
毕竟,纵是她能因着一份父女亲情而对周景帝感情复杂,但还有个权势滔天的武安侯府呢。
单若泱看了眼萧南妤,而后淡淡说道:“你先退下罢。”
耿国忠听闻此言登时心中一喜,没有当场发怒将他扭送进大牢便代表这件事有很大的机会!
或许不过还是略有些许顾虑?
对此他倒也能够理解,终究公主与他是不同的。
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单若泱才问:“你觉得他的身份可信吗?”
萧南妤点点头。
方才打从那人进门起她全程什么也没干,就顾着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了,哪怕是一个细微的眼神表情都未曾放过。
“他很努力在克制自己的情绪,但很显然,一份埋藏了二十年之久的血海深仇并非想克制就能克制得住的,眼睛里隐忍的恨意很真实。当然了,善于伪装者并非没有,不过若能伪装到这个程度,那他也算得上是个世间鲜有的能人了。”
一个是爱,一个是恨,这两种感情是最浓最烈最难演得完美无瑕的。
有句话说得就很好——有些感情便是嘴上不说,眼睛也是藏不住的。
是以单若泱其实也更倾向于相信他的身份。
终究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一个五岁的孩子跟如今一个二十五岁的成年人之间根本就是天差地别,想要从外在去判断两者之间的关系无异于痴人说梦,否则他怎么敢来京城?
如今便是官府拿着当年的画像来仔仔细细比对都无法确认。
况且定远大将军全家上下也都死绝了,更无人能够证实什么,至于那位所谓的忠仆……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
“眼下除非定远大将军从棺材里亲自爬出来,恐怕便再没什么法子能够验明正身了。”
“所以公主打算冒险吗?”
“有何不可?富贵险中求嘛。”单若泱故作轻松地笑笑。
这条路本就没有什么绝对、肯定,任何一个人都存在背叛的风险,任何一个计划都存在失败的可能,哪里有那么多万无一失?
若遇着个人遇着件事都不断瞻前顾后下不定决心……或许可能会避开很多危机,但也一定不会成功。
“既是想干票大的,适当的冒险精神总还是要有的不是。况且他又没说他究竟有什么目的,我上哪儿能懂那么多去?我不过是个心软懵懂的公主罢了,被‘故人之后’的花言巧语所蒙骗,我也很冤呐。”
这么含糊不清的一件事,可无法作为什么证据能够将那顶大逆不道的帽子扣死在她的头上。
而对于她来说,只要不是盖棺定论辩无可辩之事,就值得她去冒险一试。
“我只想法子将他送进军营当小兵,其他任何事都不会沾手,后面的路我更不会去插手,也没那能耐去抬举他多少,全凭他自己罢了。正如他方才所言那般,将他送了进去之后我便全当不认识这个人。”
“若他没那能耐,我也不会损失什么,若他不负所望自个儿爬了起来,那便是一个极好的盟友。”
萧南妤想了想,也表示认同,“咱们走的这条路本就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
两个“疯女人”向来是“臭味相投”共同进退,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恩爱两不疑”了。
“我先去看看玉儿今日的功课做得如何了,待用过晚饭之后书房见罢。”
萧南妤离开没一会儿,便有门房来报,“六公主带了一堆人意欲强闯进来,已经顶不住了。”
长公主府有亲兵把守,作为六公主的单若水也有,双方谁也没比谁强,不过到底占了个公主身份的优势,底下的人束手束脚难免落于下风。
话音才落地呢,远远儿的就听见一串脚步声越来越近,听这杂乱的动静,估摸着人是不少。
单若泱登时脸色一沉,“将府内亲兵全都叫过来。”
这时,气势汹汹的单若水已经来到了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