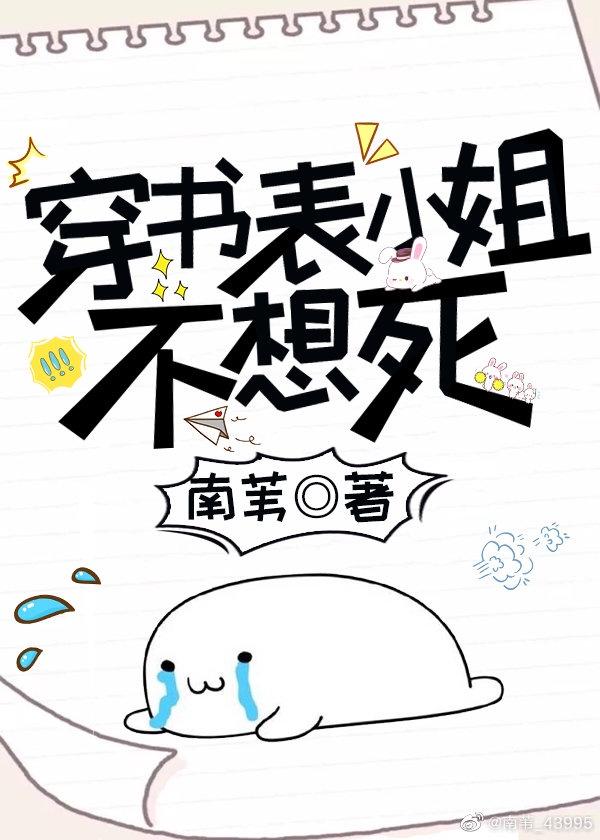墨澜小说>死对头继兄登基后 > 第19章(第3页)
第19章(第3页)
“现在知道是陛下了?刚刚怎么就忘了,还当着别人的面直呼朕名讳,你可知这是大不敬。。。”
“是大不敬的罪,臣女知错了。”霁明柔流畅的接上了燕珩说到一半的话,燕珩这几句吓唬人的话,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她都能经常听见,是以记忆深刻,接话都不过脑。
燕珩:“很好,还会打断朕说话了。”他是她用来练胆量的吗?
“臣女不敢,刚刚只是一时情急,请陛下恕罪。”霁明柔意识到不妥,立马低头解释。
燕珩绕道霁明柔面前,迫使她正视自己,似是认真似是玩笑的说,“朕不爱听这些,都是应付人的表面功夫,假的很,张嘴不敢闭嘴不敢,天天把恕罪挂在嘴边,都快说成口头禅了。”
霁明柔抬头看了眼燕珩那双眼,又匆匆低下头,思绪纷乱,那他爱听什么?又想从她嘴里听些什么呢?
燕珩这一笑仿佛又把她拉回到了几年前的时候,也就是阿珵出事之前的两年,那是霁明柔在宫里最惬意的时光。
那次竹林罚写茶经后没多久,楚行言和楚玉柔就莫名的离开书院,自那起,一切好像都不一样了。
太子是板上钉钉的未来帝王,是以所有人都理所应当的认为燕珩就该是那副端正自持、不苟言笑的模样,霁明柔起初也是这样想的。
但后来她发现,燕珩不是这样的,他是储君,也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会哭会笑,有少年人鲜衣怒马的炙热朝气,也有无聊恶劣的小心思,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喜怒哀乐,不是冰冷的雕塑。
不过,无论从前如何如何,现在他是皇帝,是九五之尊。
她或许之前并没有摆正自己的心态,所以自己在面对燕珩时并没有意识到身份的天差地别,有些心思停留在几年前。
不好,这样不好,她必须要修剪泛滥的枝丫,不能生出不该有的心思,有些东西不属于她,不能强求。
“此前是臣女冒犯,往后臣女谨记规矩礼仪,不敢再犯,谨记生疏有别。”这话是霁明柔对他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
霁明柔突然的冷漠点燃了燕珩一直压抑的火气,他往前逼近两步。
“不敢,你真的不敢吗?”燕珩顿了下,缓缓道:“满朝文武勋贵,谁敢在慌乱的时候直呼天子姓名,谁敢像你一样,情急时还会给朕下命令,你每次见着朕,有人的时候恭恭敬敬的请安,没人的时候呢?有几次能想起来请安这回事?
口口声声说不敢,说恕罪,但你真的不敢吗!没有,你从没有真正怕过!霁明柔,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不怕?是谁给你的底气和胆量,放纵你一次次在朕面前触碰规矩底线。”
霁明柔闭眼,彻底陷入慌乱中,不知说什么好。
气氛有些凝结,迅速冷滞。
燕珩抿唇,见她这幅抗拒模样,心底竟有些后悔刚刚脱口而出的话。
他不该这样冲动的。
两人相对而立,但久久无言。
许久,燕珩落寞的看向门外,妥协道:“你当朕没说过这番话。”
说罢,率先转身离去。
霁明柔无言看着燕珩离去的背影,独自在屋里又站了许久。
“郡主?我们…回去吗?”玉茉在门外敲门,探头探脑的问道。
霁明柔深吸一口气,平静下来,“回,我们走。”
既然楚行书和兮云待在一起,那就没什么必要等着了,兮云的安危也不必担忧,还是先回去的好。
她要是在这里等下去,等他们夫妻俩出来,免不了一阵尴尬。
燕兮云第二天才由楚行书亲自送回来,看样子楚行书是连朝都没有上。
无论楚行书如何说,燕兮云始终不肯让他住进公主府里,经过昨晚,长公主的怒气丝毫没有减少,只要想到楚国公夫人替楚行书纳妾的事,她心里就怄的慌,恨不得当场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