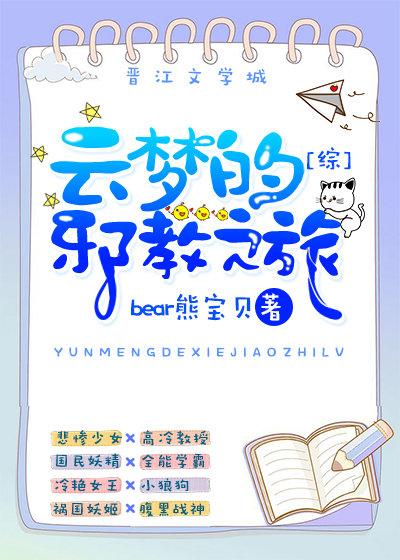墨澜小说>病弱万人嫌陷入修罗场 > 第 110 章 秋雨缠绵(第2页)
第 110 章 秋雨缠绵(第2页)
谢不为却倏地明白了诸葛登的意思,赤红的宽袖按在了黑紫色木案上,登时起身快步走近了诸葛登,并同样垂眼看着那一片枯叶。
“表哥,你适才,也去追了那刺客对不对?”
但诸葛登却仍像是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中,只愣愣地看着手中的枯叶,并不回应。
谢不为便只好再问石宽,“那你说说,县府中的长官都是如何被谋害的?”
石宽不敢含糊,连忙思忖着回道:“刺客来去无影,又都在夜间出没,无人知晓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但几位府君及上官都是在自己房中遇了害,且并无半点声息,所以我们才丝毫没有头绪。”
谢不为觉出了异常,“怎么会一点声息都无?”
石宽也很是疑惑不解,“那些刺客手法不一,有的上官是被一剑割了喉,有的上官则是中了毒,但问遍了府中所有侍卫军士,都说没有看见过有可疑之人进出几位上官的房间。”
也不知是否是门外的秋风忽起,谢不为竟觉背脊有些生凉,掩在宽袖中的手微微攥紧,皱眉沉声,“如你所说,倒像是有了鬼。”
石宽也是打了个寒颤,不自觉搓了搓手臂,“不瞒谢将军,也不是没人这么觉得过,当真是邪门得很。”
他再有一叹,“毕竟这城中,鬼魂的怨气恐怕早已冲了天。”
()谢不为顿觉荒谬,正欲低斥,却不想,诸葛登竟在此时又突然开了口。
“是女子。”
谢不为诧然看向了诸葛登,“表哥,你在说什么?”
诸葛登闻声,竟徐徐抬起了头,将手中的枯叶轻轻地插在了谢不为的玉冠边,凝目片刻,才道:“这片叶子,是从那人的发间落下的。”
他再又将枯叶缓缓摘了下来,放回了手中,“我看见了,那人的眼尾与鬓角,是女子。”
谢不为神色一凛,不自觉捉住了诸葛登的衣袖,拧眉道:
“你是说,那窥探我们的人,是个女子?”
诸葛登垂眸轻轻捏了捏枯叶,发出了细微的“咔嚓”之音,又突然没了声。
但谢不为已算是明了诸葛登之意,便不再追问诸葛登,而是眉动稍思,“竟是女子吗?”
可一旁的石宽却又失礼出言,“不可能!那些刺客绝不会是女子!”
谢不为并未计较许多,只狐疑地看向了石宽,“为何不可能是女子?”
石宽却有些答不上来,支吾了半晌,才道:“若是女子,怎会有如此大的本事,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谋害了县府中这么多大人。”
话出又觉单薄,连忙低声补道,“况且城中女子,除了那些富户家中的夫人女儿,多半也已经唉。”
谢不为并不认同石宽的前半句,但念及后语,也是不解,缓缓走回了孟聿秋身边,本能地牵住了孟聿秋的手。
似问似忖,“阿姊也说了,城中大多是老弱妇孺遭了难,可表哥又说窥探我们的人是个女子,那我们该如何去查?”
不等孟聿秋出言,又再道:“此事又不能放过,不说我们二人或是表哥的安危,只说这刺客一日不除,人心便一日不会安定,也就无人再敢来鄮县为官,城中秩序也不会有稳固的那日。”
再是一叹,语速疾疾,“还有舟山上的海盗,即使那些海盗已经暂时闻风而逃,但他们必然是在暗中窥视我们,如今敌暗我明,我们更不知这海盗究竟是什么情况”
“鹮郎。”孟聿秋忽然掌住了谢不为的脸,指腹轻轻按住了谢不为的唇角,“不要慌张,我们一件一件慢慢来。”
随着孟聿秋语落,有门声“吱呀”。
是随行的侍从见此情状便主动领着堂内众人一同退下了。
室内更昏暗了些。
但谢不为却莫名安心了不少,徐徐靠入了孟聿秋的怀中,语速也缓了下来,“我知道,这些事是一样也急不得,但我却丝毫没有头绪。”
孟聿秋抚着谢不为的背脊,温声如和风,“如今最为紧要之事已经交代他们去做了,刺客之事也有了头绪,若当真是女子,其实已算是线索。
至于舟山上的海盗,他们畏惧我们带来的军士,在有了确切把握前,便不会轻易有所动作。”
谢不为霎时抬起了头,“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孟聿秋拂过了谢不为额角鬓边的